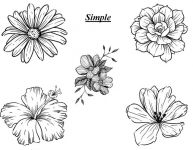我的父亲母亲散文随笔
一

父亲和母亲是一个村的,父亲大母亲八岁。母亲高高的个子,模样周正。父亲应该说也很英俊,但因为小时候的一场病,烧坏了一只眼睛,一只眼睛视力很弱,这并不影响父亲干活。父亲很能干,种地是把好手,手也很巧,头脑也灵活,所以我家的日子还算殷实。
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父母的爱情故事,是听姥姥讲的。姥姥说母亲要嫁给父亲,姥爷说什么也不同意,说要打断母亲的腿。一向温和的母亲铁了心了,最后姥爷把母亲赶出家门。母亲出嫁那天是从三姥姥家出的门。结婚一年,姥爷不让母亲进家门,直到有了我。姥姥太想母亲了,就偷偷去看了母亲,然后带着母亲,抱着我去见姥爷。姥爷见到襁褓中的我,心软了,接受了母亲,也接受了父亲。
父亲很宠母亲,从不让母亲干重活。地里的活几乎都是父亲一个人干。因为父亲的宠,母亲单纯而清浅,高兴时会唱歌,还会在屋子里跳起秧歌舞,每每这时,父亲会眯着眼冲着母亲笑,一边笑一边对我们说,看你妈呀,这个疯啊。很长时间,我都觉得母亲不像个历尽沧桑的妇人,倒像个不经世事的少女。
母亲一下子成熟起来是在父亲的一场大病之时。
我生了儿子后,母亲来家里伺候我坐月子,父亲独自在家。父亲好着的一只眼睛突然看不清东西了,生性要强的父亲起初没和我们说,直到他完全看不见了才告知了弟弟。母亲离开月子里的我,陪着父亲去看病了,从市院到北京,母亲一路相随。在北京的手术很不成功,不久父亲的眼疾又复发了,父亲几乎要放弃了,我们不肯,母亲也不依,最后在市院动了第二次手术。手术还算成功,父亲的视力有所好转。我坐完了月子来医院看父亲,父亲正处于恢复阶段。我看着母亲小心翼翼地牵着父亲的手,神情凝重得让我陌生,那种感觉她和父亲不是夫妻,而是并肩作战的战友,无论父亲处于多么危困的境地,她都要挺身将他救出。
出院后,父亲的视力也只有零点几。那时父亲承包着一块好几十亩的水田地,七年的合同,刚刚种完了四年。父亲健康时,从不让母亲下地,地里的活是父亲和小工们干的,母亲只负责给小工们送水发钱。父亲说,多花一个小工的钱就把母亲解放出来了,用不着母亲干活。父亲因为视力模糊不能到地里干活了,因为水田地正常人穿着水靴都有可能摔跤,这回是母亲坚持不让父亲下地了。身体瘦弱,一向不怎么下地干活的母亲突然就泼辣起来了,她领着小工们插秧、拔草、打药、施肥,因为是东家,她得样样干在前面。一次,我回娘家,父亲说,母亲在地里给水稻上水,带饭了,中午不回来。我到地里寻母亲,远远地,我看到单薄的母亲扛着一把铁锹,站在水田里。水泵呼啦啦的响着,泵口喷溅着四射的水花,水从水沟流到敞开口子的稻田里。过去,我见过父亲摇发动机带起水泵浇水的情景。一向大力的父亲摇起发动机都很吃力,我难以想象瘦弱的母亲费了多大的力气才把这发动机摇起,想着想着,就流起了眼泪。母亲远远望到我,扛着锹往回走,身体摇摇晃晃,她走着的是一条窄窄的、泥泞的沟边,上面曾经留下过父亲太多太多的足迹,如今,母亲的脚印叠加在这些足迹上,这些足迹便生动起来、温暖起来,然后隐没在岁月的长河里。
从小到大,我都觉得父亲像一棵大树,母亲、我、弟弟三人是栖居在树上的三只鸟,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,为我们驱热阻寒,我们在枝叶间安享着父亲为我们精心烹制的太平盛宴。忽然,大树枝叶萧条了,我以为我们会慌乱、会手足无措,没想到母亲“腾”的一下子就撑开了翅膀,护住了我们,也护住了她栖落的那棵树。
二
父母娇宠我和弟弟。无论我们犯了什么错误,从没打骂过我们。我自小成绩优秀,又极爱读书、画画。父母把我的奖状和我画的画一并小心翼翼地贴到墙上,他们看着很舒心、很骄傲。父母不让我干任何活,十几岁时,同龄的`孩子们挑菜、喂猪、做饭,个个都是父母的好帮手,我却什么也干不好,所以左邻右舍包括一些亲戚都给我起个外号叫“大小姐”。我到县城读高中到省城读大学回来,大家见了我就跟父母说,你家大小姐回来了。我参加工作后,别人再这样叫,我就甩脸子,渐渐就没人这样叫了。
记着小时候,家家的炕上都只铺着一个炕席,硬硬的。晚上,父亲驮着我在炕席上爬来爬去扮大马。我在父亲的背上很欢快地笑,手里攥着爸爸从远处买给我的塑料小娃娃。清晰地记着,那小娃娃是粉红色的,梳着两个小辫子,怀里还抱着一个大玉米棒子。母亲在煤油灯下一边纳着鞋底,一边瞅着我们爷俩笑。煤油灯发出黄晕的光,很柔和,光晕里仿佛也藏着笑意。
从小大大,对于我们姐两提出的要求,父母总是竭力满足,从不亏着我们。父亲常说,我这两个孩子,从小,他们爱吃什么,我都让他们吃个够,唯恐他们不解馋。弟弟上初中时,刚买的自行车骑了半年,就想要一辆山地车,父亲二话没说就带他进城买了。弟弟高兴,父亲就觉得很满足。父母都没什么文化,他们不懂教育方法,不像我有了孩子后,卢勤、尹建莉等的书买了一大堆,他们对我们的教育原则后来我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出:子女高兴,他们就欢喜,只要子女高兴,他们无条件的满足。这样做是有风险的,但我的父母是幸运的,我和弟弟都没被宠坏,我们都善良、孝顺、勤勉、踏实。因为父母一面宠着我们,一面用他们的善良勤劳质朴宽厚无声地影响着我们,父母的言行本身就是本无字书,我想我和弟弟是开了天眼的,这无字书我们能读懂。
三
父母住三间房子,弟弟一家在另一处住着四间。父亲念叨说想盖新房子,我和弟弟出于孝顺都很支持。一天,父亲把他的心事透露给我。父亲说,他比母亲大,肯定走在前面,头走他得为母亲安排好,房子是第一要紧的,母亲住的首先要舒心。我说,我会把母亲接到我家里。父亲说,住楼太憋闷,母亲又没熟人,我们上班了,母亲会太孤单,就让母亲在自己家里。
房子盖好后,父亲院里院外的收拾,买了两千多块钱的土,把院子垫高一些、垫平一些。院墙怎么修、新厕所盖在哪,他都一一设计,忙得兴致勃勃。邻居们都说,这老爷子真讲究。我和弟弟都知道,父亲所有的忙碌都是为了母亲。父亲和母亲的字典里或许没有“爱情”这个词,从小到大,我没听他们说过。我知道他们把这个词放在了柴米里、放在了油盐中,放在了一起过活的日子里。
年纪大了,父母不再侍弄田地了。母亲就到一个观光园里喂鸡。母亲勤劳、厚道,干活从不藏奸耍滑的,所以一起干活的人陆续被辞掉,换成新人,唯独留下了母亲,且转为正式职工,享受福利、奖金等待遇。父亲也不肯闲着,勤劳了一辈子,他说闲下来人不舒服,就在家里侍弄了二十多只羊,一年下来卖到一万多元钱,父亲一如年轻时把钱交到母亲的手里。母亲笑着说,老家伙还挺能耐,父亲的皱纹里便盛满了喜悦。
休息日,我买了北京烤鸭去看父亲。吃饭时,父亲先扯下一只鸭腿放到碗里,送到餐厨里。不说我也知道是留给母亲的,母亲中午在观光园吃饭不回来。吃饭时,父亲和我悠悠地说着话,话题还是离不开母亲。他说,我和你弟弟说了,我和你妈两人时,不用他操心,我们身体都挺好,要是剩你妈一人了,他每天至少得来看一次,有些话啊,我得提前嘱咐你们。我说,爸,你老说这些干啥啊,说得人心里不好受,我要你们都高寿,和我一起哄你的重外甥。父亲笑着说,傻孩子,人老了,不求高寿,高寿了会给儿女添麻烦。父亲不算老,属狗,今年虚岁68,我就纳闷,他的记性真差,他怎么就忘了,我和弟弟小时候给他们舔了多少麻烦呢。尤其是我,自小多病多灾:三岁时,小姑和三叔闹着玩,一把剪刀穿到了我头上,离太阳穴不足半厘米。母亲捂着我的伤口,父亲拼了命地蹬着自行车把我带到乡医院里,医生说,父亲的骑车速度再慢一点,我的小命就呜呼了;十一岁那年,我急性阑尾炎化脓,住进医院,手术后我昏睡了四个小时,醒来了,看父亲蹲在我床边,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。
父母都是茫茫人海中的小人物,但在我心中,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灿烂的人。他们的爱和爱情,都是润泽我生命的玉露琼浆,会让我享用一生、回味无穷。